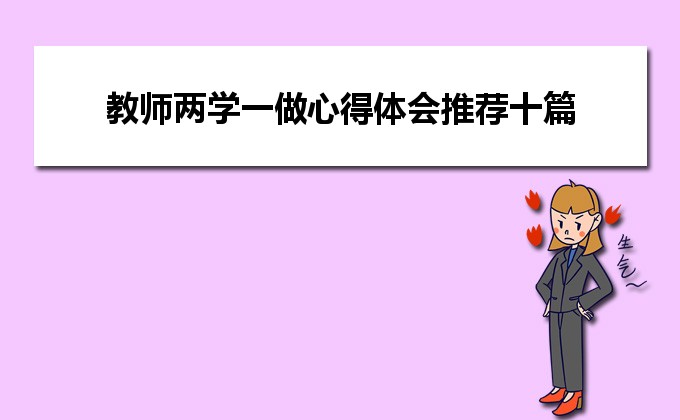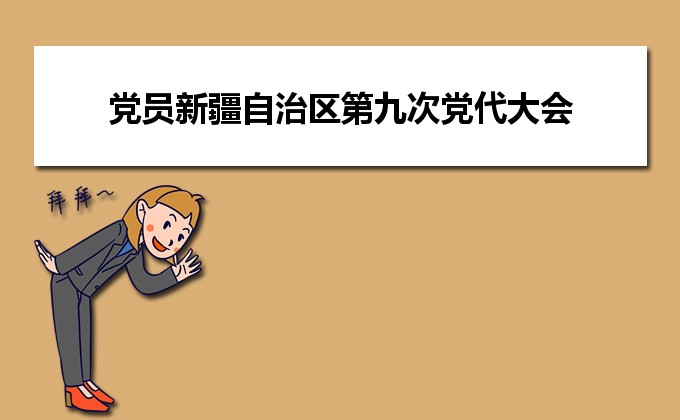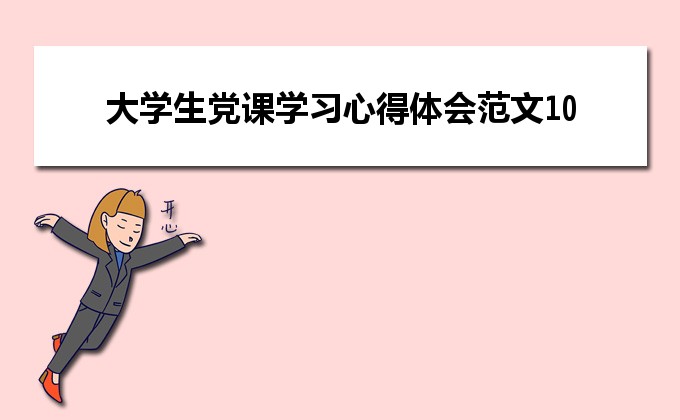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轰动了整个文坛的时候,有位诗人写了以《致路遥》为题的诗作,高度表达了对路遥的敬畏。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第一次造山运动
挺立在黄河汹涌的臂弯
你同月亮一起升高
又跃上太阳穿刺重围的黑暗
陕北民歌飘逸豪放的任性
交响乐朦胧而抽象的内涵
母亲的呼唤和幼儿的泪眼
饥饿的乡童和补丁满身的老农
蚯蚓在不停地蠕动
愉快地死去又痛苦地复活
创造弯弯曲曲的历史
永生的天才在没有道路的道路上
走向没有终点的终点
对于我们所处的这个现实社会,就是再激烈的批评,也是一种爱心的闪现,就像一个医生对他的病人一样,必须诊断准确,并且说出事实的真相,才可能对症下药,铲除病根,使病人恢复健康。
路遥在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里,是这样评价“文化大革命”的:“既是立法的议会,又是执权的政府,这是一些胆大而激烈的人物,革命的暴风雨刚席卷过社会,他们就露出了头角,站在这场革命的前列冲冲杀杀。他们的性格特点如果能打比方的话,可以这样说,要盖一座房子,他们也许都是些笨蛋;如果要拆一座房子,他们会比谁都拆得又烂又迅速。”路遥的深刻,常常让人惊讶,他的收获一定是来自他那颗哲学的头脑。在“文化大革命”那样大动荡的岁月里,人们就是这样肯定着自己和否定着自己,在灵魂的大搏斗中成长或者堕落,都是瞬间的事情。路遥深知一个为真理献身的人是伟大的,也是一种大爱,他赞美为正义挺身而出的英雄的同时,将自己也谱写成了英雄。英雄就是敢于把头颅献上祭坛的人,让人类来收获他的智慧,让历史收获它的精神。
路遥写《人生》反复修改了三年,前两次都因为不满意而撕碎了,直到1978年才完成。当时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不分昼夜,浑身就像燃起大火,口舌生疮,大小便不畅,常常因为写作,一个人在深夜里转圈儿。我们知道,如果说收获的话,路遥的收获来自他高尚的认识能力和崇高的目标,以及超越常人的吃苦精神和牺牲精神。
路遥创作的准备工作以及精细的谋篇布局,在目前作家中无人能与之相比,路遥给中国文学创造树立了一个典范,《人生》的价值,就是把当时好人坏人脸谱化的程式彻底颠覆。把人性的多面性展示出来,使人物描写走出单一的格式化。把当时社会条件下青年人存在的问题和尖锐的矛盾,第一次摆到了人们面前。
当然一百个作家就有一百种写法,但不可能一百种写法都是最好的,最好的往往是能够代表大多数人立场的作品,它既是本民族的,也是其它民族的,也是世界人民的共同心声;它可能是现实主义写法,也可能是后现代主义写法或者是其它什么主义,但有一点是必须的,一切主义都是从现实主义或者叫现实的生活中产生的。就好像所有的庄稼都生长在大地上一样。路遥是现实主义作家,但他的思想更多地反映出了现代主义的艺术光芒。
若要让一个祖国强大起来,就是要让每一个个体觉醒。路遥的小说并没有空洞地去描述无边无际空泛的大道理,而是始终关注和鼓励个体的追求。如果每一个人都在追求真理,每一个人都在改变原有的生活条件,每一个人都在富裕和文明,那么这个国家就会迅速地改变。
路遥总是以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说话,在具体的事件中展示真善美,在他的笔下没有绝对的坏人,这些人的语言和行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展开。路遥的创作决不脱离现实,总是活灵活现地反映生活中的真实,并且把他们上升到艺术的典型化之中。《人生》的成功,在当时已经远远地超越了当代中国文学,它带着生活的气息走进校园,走进知识界,走进工厂和农村,走进每一个读者的心。
对于路遥的文学成就,以及路遥这个人,我们不能就事论事,你喜欢他,他也不可能是你的;陕北人喜欢他,他也不是陕北的;中国人喜欢他,他也不全是中国的,他应该是世界的。任何一种文化现象扩大到一种社会现象时,它的本质就产生巨变。任何一种地域化的解释都是弱小的,甚至是无力的。
在俄译本《人生》后记里,谢曼诺夫这样写道:“我看到过根据路遥小说改编的电影,这部电影在世界各国放映,电影是感人的和富有特色的。最后,我在中国和作家路遥本人会见了,他是一位纯朴的,同时又是一个聪明的,善于思索的人。他已经是陕西作家协会的副主席。”是的,路遥一路走来,确实艰难,但是他创造的辉煌也是一个可观的高度,这个高度又是用思想的积累凝结而成。这位外国友人敏锐地发现路遥作品里的精神内涵,路遥的另一个重要思想,就是“民族的根首先在农村”。路遥认识事物本质的能力是超前的,他认为“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孤立的,是和整个社会密切相关的、互相折射的,有些作品尽可以编造许多动人的故事,但它们没有关注人物的精神世界,如果人在作品中只是一个道具,作品就不会深刻。欧洲有些作家,包括大仲马为什么比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低一筹,原因就在于此”。
我们每一个人都想看到更多的天空,踏上更多的土地,而心灵的宽广也许对一个正直的人而言会更重要,路遥比别人获得了更多的珍宝。虽然路遥物质并不丰富,就算他一个人脱贫了,而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呢?就算他的家族脱贫了,而那个广阔的黄土高原呢?路遥多年来心灵的负担正在于此,他没有只想自己,他想到的是一个陕北,一个贫民阶层,一个民族最基本的生存状态出现的重大问题,在陕北十年九旱的现实生活中,不是谁能在一夜之间改变了的,而更大的问题是,我们的态度、方向、意志和情感的衰竭。人从本质上讲就是历史,但把握现实的创造,解决现实的生存能力永远是问题的关键。如果盲目地崇拜现实也是会犯错误的,我们的一些作家就是犯了这个错误,既不了解历史,又不懂得现实,那肯定是没有未来的,未来是历史和现实准确判断的结合,才能有正确的决策,赢得未来的成功。路遥的创作观念有很多珍贵的东西,其中超越土地和农业,崇尚科学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农村的现实和他的理想之间的差距,常常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整个20世纪的中国,前半个世纪在战争中度过,而后半个世纪前半程基本搞了政治运动,经济上贫穷落后,人民受尽苦难。路遥的创作思想,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形成并且成熟起来的。路遥一直寻找自由的空气、自由的空间、自由的精神,但遗憾的是,自由的土地在哪里?路遥是一个富有开拓性和创造性的作家。他热爱土地,赞美劳动,但永远诅咒贫穷落后,他在小说《人生》里让高加林说出他自己想说的话:当他的恋人黄亚萍问:“你想不想去?”高加林不假思索地说:“我联合国都想去!”路遥对新思想,对现代化、对科技革命充满了希望。一切外部世界的变化都在他的视野之中,并且在作品中有重要反映。
1988年,台湾作家柏杨先生来西安,他就是著作等身,并写出《丑陋的中国人》的作者。路遥代表陕西省作协与柏杨先生和他的夫人诗人张香华女士会面。他们的会面留有照片,不知道这两位同样有着深厚思想的作家谈了些什么?但他们都太爱国了。一个以杂文为武器鞭挞丑恶。一个以小说作为武器批判现实。他们都是努力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人,而不是被别人掌控或玩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