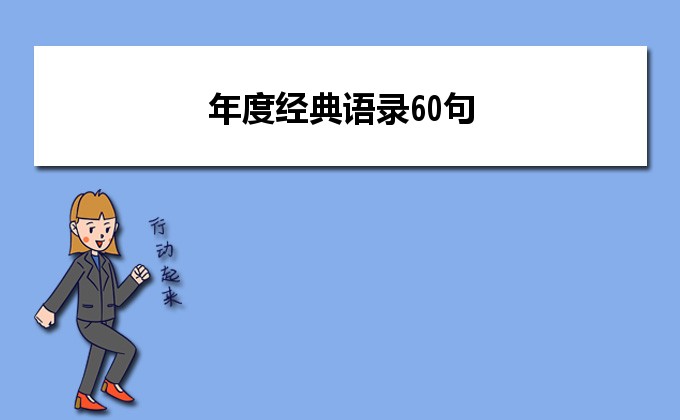语不惊人死不休 王朔各个时代的经典语录
语不惊人死不休 王朔各个时代的经典语录
1、你演得很好啊,装纯,本来就是你的路子。
2、观众很可爱,观众能吃粗粮。
3、平时大家都装,不装早打出脑浆子来了。社会,就是一帮人在那儿装呢,谁不装,有人找你聊。人类就是装着装着,才进步的啊。
3、人挡着我,我就给人跪下———我不惯着自己。
4、这人太讨厌了,不接电话就是告你我不爱接———我就不能让他觉得有志者事竟成。
——以上来自《梦想照进现实》
5、全国一年只放一部电影,大片和大片还互相躲呢。放俩,今年就太热闹了。没什么见识的小报记者就得满世界嚷嚷有擂台。还不如样板戏呢,那还八个呢。
6、本来挺浅一池子水,前两年开始往外冒所谓国产商业大片——所谓美元上了千万的,亚洲一线红人到齐的,吊起来打的,宣传忠孝节义的。遭到狂宣,争挂票房红旗,好象中国人忽然会拍电影了,忽然爱看电影了。
7、我觉得贾樟柯同志成熟得太快了,他的访谈已经超过了他的电影。他越坚定自己要什么,越像一个八十年代的校园精英,无比正确但属于强行跟人民站在一头的。
8、导演是所有艺术门类中最不真实的人,他就是一个总汇,是一个整合资源的人,设计打法的人,相当于部队打仗时的参谋长。司令是制片人。参谋长臭点,司令坚决,士兵英勇,仗还是能打的。
——以上来自《“收获”王朔与孙甘露对话》
9、“那时作家比导演红,一个年轻导演傍上一个好作家,拿着剧本一拍就红了,作品也不寒碜啊。陈凯歌、张艺谋的都是好作家改的。到他们(自己)做的时候,就成了《英雄》。”
10、“我觉得他(张艺谋)风风火火的,从1988年到现在,都20年了,可以歇会儿了,世界你也跑遍了,虚荣你也尝尽了,可以荫庇后人了,你60的人,跟20的人怎么争啊?他怕这个声望下去,而且他是一个陕西人,很倔,你越说我不好,我越做给你看。”
11、“当代中国电影的确缺乏好故事,不过原因不全是编剧能力问题,而是整个中国原创小说的疲软。”为《黄金甲》担任编剧的卞智洪认为,王朔关于剧本和电影关系的评价特别有道理,电影依赖剧本,但编剧不该为剧本差负全责,“即使是在好莱坞,电影也从来都是脱胎于流行小说、经典舞台剧,甚至是翻拍成功电影旧作,很少看到无中生有的东西。”
12、在卞智洪看来,优秀原创故事的稀缺也是张艺谋选择改编《雷雨》拍摄《黄金甲》的原因。“哪个编剧不想改编成熟的小说题材阿,可我们这个时代缺好小说”,卞智洪认可王朔“电影故事不如90年代”的言论,因为“你想想,1985年到1995年那可是中国文坛最活跃的10年,社会处于剧烈的变革时期,思想刚刚从禁锢中解放,王朔说中国电影史上奉献出《阳光灿烂的日子》、《外婆桥》、《红樱桃》、《红粉》的1995年是巅峰的一年,可这哪一部电影后面没有一部成功的小说,说到底,1995年的辉煌是中国小说界黄金十年反映在电影上的‘井喷’”。
13、不过,卞智洪表示,导演才是电影工业的核心,即使在上个世纪末也不能简单说“作家比导演红”,因为“电影依赖于导演对剧本和整个创作团队的掌控力”。好比当年张艺谋也看中了《动物凶猛》,但他最后自认为拍不了,因为气质不符合,这本子到了姜文手上就成了《阳光灿烂的日子》。“王朔关于现阶段电影的很多问题看得很清楚,对几位导演的评价也有中肯的地方”,但是卞智洪认为导演有探索和创作的职责,也不可能因为缺乏完美的故事就完全停止创作,“王朔他自己都认为自己进入了‘蛰伏期’,其他人更不可能有好作品了啊。有时候不能对所有人苛求太高,王朔本人可以选择蛰伏,但是对其他导演来说,不应该去否定他们继续尝试的努力,裹足不前也总是不对的。”
1、王朔《玩的就是心跳》——
和你们比起来我们是显得顾虑重重、优柔寡断,这和我们成长的时代的影响有关。我们为个人追求时不像你们那么大胆、一无所有却勇气十足、我认为值就不惜一切;我们考虑问题时更多的是注意到和整个方面的平衡。我们受教育一贯是把个人置于一种渺小的境地。这是我们的悲剧也是我们的习惯,很明白却无能为力。
2、王朔《动物凶猛》——
我感激所处的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学生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不必学习那些后来注定要忘掉的无用知识。我很同情现在的学生,他们即便认识到他们是在浪费青春也无计可施。我至今坚持认为人们之所以强迫年轻人读书并以光明的前途诱惑他们仅仅是为了不让他们到街头闹事。
在我少年时代,我的感情并不像标有刻度的咳嗽糖浆瓶子那样易于掌握流量,常常对微不足道的小事反应过分,要么无动于衷,要么摧肝裂胆,其缝隙间不容发丝。这也类同于猛兽,只有关在笼子里是安全的可供观赏,一旦放出,顷刻便对一切生命产生威胁。
我又羞又急,渐渐萌生出一种难以遏制的愤怒,真想抄起个什么沉重结实的东西扔过去,以惊人的“豁啷”一响和满地粉碎的结果来表达我的感情。当然,同我鼎沸欲喷的情绪恰成鲜明对照的就是我身体的一动不动。
本来以为父亲会非难我,孰料他竟意外的态度诚恳,并无疾言厉声,基本属于娓娓动听和循循善诱。他告诫我年轻的时候应该把精力都用到学习上去。要树立远大理想,要有自己人生目标,当然这目标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当时惟一的;做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他表示他和其他很多我不认识的人都对抱有殷切期望。似乎他们认定我将来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而这点在当时我自己一点把握也没有。
我一点也不感动,不是施教者不真诚抑或是这道理没有说服力,而是无法再感动了。类似的话我从不同渠道听过不下一千遍,我起码有一次到两百次被感动过,这就像一个只会从空箱子往外掏鸭子的魔术师,你不能回回都对他表示惊奇。另外我也不认为过份吹捧和寄予厚望对一个少年有什么好处,这有强迫一个体弱的人挑重担子的嫌疑,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造就一大批野心家和自大狂。
他们唱的是那个年代很流行的俄国民歌《三套车》,歌词朴素,曲调忧伤。在月朗星疏、四周的山林飒飒作响的深夜,听来使人陡然动情,不禁叹息,无端有遗珠失璧之慨。我至今有所不解;中苏两国的民族经历是那么相似,为什么两国的民歌传达的精神实质那么不同?我们的民歌总是欢快的,要么就是软绵绵的伤感,偶有悲凉也是乘兴而抒,大概我们的人民个个都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所以如此吧。
为什么我还会有难以排遗的寂寞心情和压抑不住的强烈怀念?为什么我会如此激动?如此敏感?如此脆弱?
我在清澈透明的池底翻滚、爬行,惊恐地挥臂蹬腿,想摸着、踩着什么紧硬结实的东西,可手足所到之处,都是一片温情脉脉的空虚,能感到它们沉甸甸、柔韧的存在,可聚散无形,一把抓去,又眼睁睁地看着它们从指缝中泻出、溜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