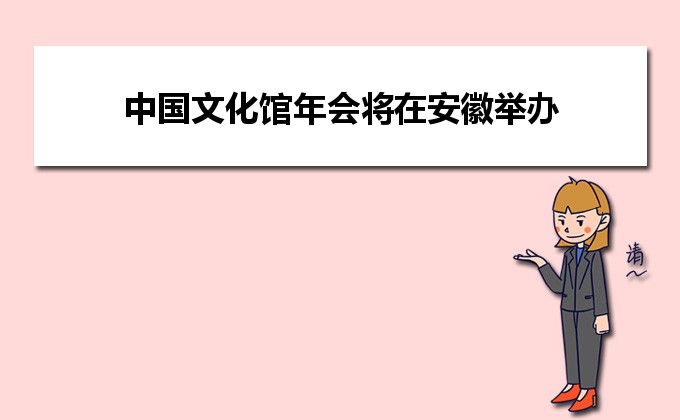李方膺诗扇面 杨频 书
去成都。
公共汽车轰鸣中,同车的乘客用方言交谈着,我什么也听不懂。我想起在四川的好朋友杨频,打个电话吧。那时候杨频从北师大研究生毕业,在南充的一家医学院教书。
有一段时间,我习惯一个人开始一段旅程。那次,在绵阳住下,看地图,有个叫江油的地方,介绍说是李白故里。距离不是太远,就打车直奔江油。在青莲镇,有碑林,写满了李白的诗歌,建筑大抵都很新,唯有古木苍翠,青苔默默。我独坐在树下,一个轻声细语的女孩问我:需要导游吗?我正要拒绝,旁边一个女子说,她会唱李白的诗歌。我买了一本她推荐的李白诗集,边聊天边听她解说。听说我从北京来,她话多起来。
我在北京待过几年,春天的风沙呀可大,又干燥。
你为什么回来?
北京的天气对皮肤不好。我看了她一眼,在林间,她脸上的光泽如同月色。她笑了,然后说,我父母都在江油。
她清唱起李白的诗歌,悠扬婉转,如同叶子上跳动的微光。
别来几春未还家,玉窗五见樱桃花。
况有锦字书,开缄使人嗟。
至此肠断彼心绝。
云鬟绿鬓罢梳结,愁如回飙乱白雪。
去年寄书报阳台,今年寄书重相催。
东风兮东风,为我吹行云使西来。
待来竟不来,落花寂寂委青苔。
她唱了好几首,自己也沉浸其中了,或许她想起了北京的朋友和自己曾经的远行。一切犹如梦境,这应该是我听到最美的声音了。我对青莲镇恋恋不舍起来,但江油已在身后。我离开绵阳,搭公共汽车去成都。汽车轰鸣声里,那婉转的声音犹在。
打完电话,我就有点歉意。杨频兄听说我傍晚时分会到成都,执意要从学校赶过去跟我会合。他说,不是太远,有高速。成都之行突然变得确定起来,杨频兄打车从两百公里之外的地方赶来,替我安排食宿。我们通宵夜谈,他聊起他的工作和学术研究,聊他对未来的设想,我说了些对书院文化的了解。那时候,我正整理一些关于书院的资料,策划出版书院的图书。他在医学院的工作也算安逸,“长安米贵,居之不易”,但对他而言,北京的文化吸引力仍然足够大。杨频兄老家是阆中,那是一个文化圣地,我曾经在他的朋友圈里看过他儿时学堂解元中学、东岭书院,古柏苍劲,唐代曾出过状元兄弟尹枢尹极,时称“梧桐双凤”,那些关于状元的故事和遗迹应该是他童年到少年时代绕不过去的“负担”。如今,他题写的对联挂在东岭书院的门口,“人杰地灵梧桐双凤传奇在,斗转星移兹院英才四海贤”。这是文雅的说法,通俗是这样说:“小时候在树根上展开战场,弹杏子核,斗烟牌,如今小伙伴们星散四方……”
凌晨不知几点才睡去,第二天早起上青城山,看那些曾经进入张大千笔下的山色云霞。我记得在远山上,有几株红叶子的树跳出葱绿的背景,极为夺目。快乐的是,我们饥肠辘辘地在山顶附近痛快地吃面。
离开青城山、都江堰,我又独自上路,去看乐山大佛,游览峨眉山,又有一帮萍水相逢的媒体朋友在乐山会合。夜晚,我在乐山大佛附近的江边,江水平缓,三两点渔火。我想起回到南充的杨频兄和他的远行梦。
后来,杨频兄重回北京读博士,又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他的远行的梦想一一实现。有时候,我在想,他离开老家的夜晚,会不会记起李白那首著名的诗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我倒是希望,那种轻快和欢悦的心境会在那个夜晚涌现。负笈京华是一个听上去很美好的词,但其中的艰辛大约只有个中人才能体会。有时候,人生是一场自我的叙事,那些遥远的未来,因为内心的构思而充满吸引力。而我忘记了那些故事,只记得一些微小的细节。
有一次,杨频和郭睿两位兄长来家里喝茶,他们两个谈艺术,我大约只有烧水倒茶的份儿。不知怎的,聊得了诗歌,聊得兴致盎然的时候,我拿出海子的诗集,各自谈起喜欢的诗歌。杨频低声吟诵起来:
我在一个北方的寂寞的上午
一个北方的上午
思念着一个人
我是一些诗歌草稿
你是一首诗
我想抱着满山火红的杜鹃花
走入静静的跳伞塔
海子诗歌里很多词汇,温暖而亲切,又略含忧伤。杨频兄似乎不是擅长吟诵的人,但那时的声音沉静而绵长,海子诗里的一个个词语,像饱满的麦粒,在地上跳跃。余音绕梁,我突然明白这个词的意思。那次,杨频兄带给我一幅字,是我请他写的,“慈悲喜舍”,笔下有悲悯。
杨频兄的书法,我尤其喜欢尺幅不大的作品,如同中国的亭台楼阁,结构精美灵巧而又稳重,有时候,字写到酣畅淋漓处,笔画突然变得奇崛,犹如危崖独立的亭台,见之,心惊,心喜。杨频兄的书法是那种一眼就能觉出书写者才华的类型,有略微张扬的用笔。现在看来,那些张扬的才华背后或许有淡远的焦虑,文化上的、生活上的,这些张扬是一种对抗,抑或是一种思念。
浮生若梦境,到者愧钟声。这副峨眉山寺的对联,是对我虚度人生的警醒。杨频兄从东岭书院到故宫博物院的路途,可谓遥远,有艰辛又有快乐。其中的付出和收获,大约都化作了书写时的平静,这或许是感受古典文化的辉光必须要经历的磨砺。而且,从朋友处听到越来越多的好消息,有学术成就,有买房的消息,远在故乡的孩子也大了,或许不久就来京团聚。
不久前,我请杨频兄写《与朱元思书》,挂在书房。那是一幅酣畅淋漓的作品,尤其写到最后,疏朗、清丽,笔画“疏条交映”,以渴笔的质地表现潇逸的气质,犹如晨光里的山河,山光云影,俱有喜态。近日,杨频兄微信发来一段小字心经,见了心生欢喜。杨频兄的书法愈来愈洗尽铅华,犹如老僧入定,静如止水,穆若清风。他说,一动不如一静。或许,我们不知道到底是日日夜夜的书写塑造了我们,还是我们内心的静穆塑造了书写,但最终一种圆融会包裹我们,让我们感到轻松和喜悦。
杨频兄在北京的书房叫甘雨堂,在城市的夜里,那是一个闪烁光华的地方。我曾在那里停留,喝茶。月华如水,喧哗声渐远,那一刻,我忽然记起了那个叫青莲镇的地方,记起了那个女子清唱的歌:别来几春未还家,玉窗五见樱桃花……是啊,那些春天,那个花开花落的窗前……
在甘雨堂废纸如山的书写里,杨频兄会不会偶尔写到杜甫的那首《月夜》:今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