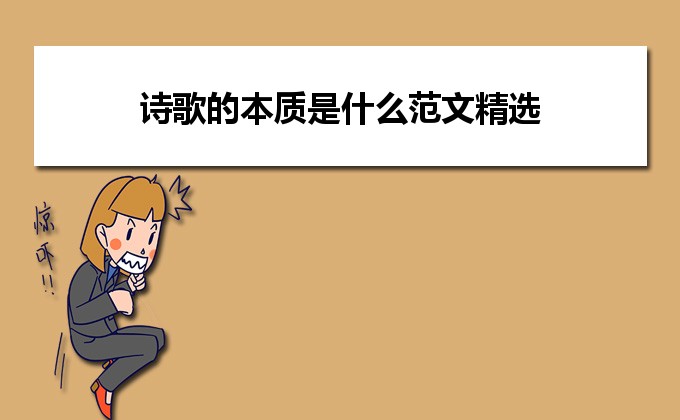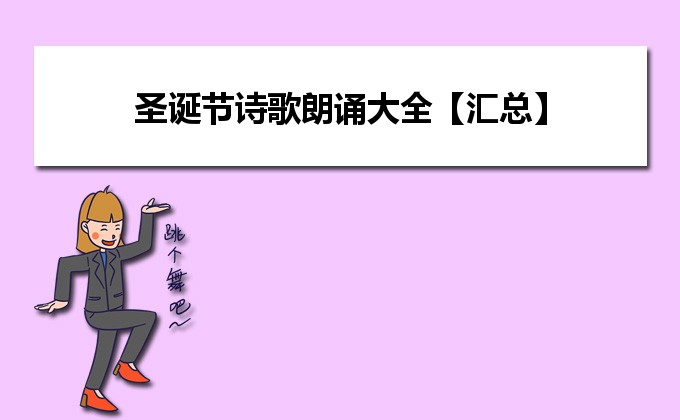在我们生存的世界里,人类意识的符号有两种:一种是认知性的逻辑符号,一种是感知性的表现符号。前者属于科学,后者属于艺术。两者都是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一个是实用的,一个是审美的。而语言既可以作为认知性逻辑符号系统,也可以作为感知性表现符号系统。下面一起吧看看吧!
它有两种:一种是日常语言,一种是艺术语言。日常语言就是我们的普通会话语言,它是告知性、实用性的,艺术语言则是表现性和审美性的,是在前者的基础上构成的更精练、更有审美表现力的语言。而以文字为手段的诗,它的语言是至精至纯的文学语言,是最高的语言艺术。这是说,诗歌的语言除了具有一般文学语言的特征和美感外,还必须具有内在征服力。这种力量是隐形的,是从表面找不到的但又深藏于语言背后的意蕴和精神。诗是表现看不见的,只可想见、悟见的东西,如心灵、道德、情操等。诗不仅仅在于表现什么,而是在于意味着什么,即隐含在语言符号之中的意义。
一.诗歌语言的情感性
苏珊朗格说:“当人们称诗为艺术时,很明显是要把诗的语言同普通的会话语言区别开来。”这种区别,当然不能在其语言的要素――语音、语汇、语法等方面做文章,也不能简单地把二者的区别归结为诗有格律,散文没有格律。鉴于此,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语言的表层进行比较,而应深入到内核,从两种文体的语言与作者心灵世界的关系上进行考察。
从视点的角度看,诗与散文(广义)是异质的。所谓审美视点,“就是诗人和现实的反映关系,或者说,诗人审美的感受现实的心理方式。从审美视点观察,文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外视点文学,即非诗文学;一类是内视点文学,即诗和其他抒情文体”(吕进语)。内视点也称心灵视点或精神视点。简单地说,诗关注的是内在世界,表现的是诗人内宇宙的形貌和色彩;而散文关注的是外在世界,描绘的是外宇宙的形貌和色彩。因此,散文语言力图尽量准确、鲜明、生动地表现事物的本来面目,从而使抽象的文字符号产生逼真的艺术效果。客观性是散文作品的基本特征,外视点是散文的“身份证”。而诗歌恰恰相反,它不注重对外在世界的描述,而是致力于抒发诗人的主观感受,它是外在世界的内心化、体验化、主观化、情态化。诗歌对客观世界的观照主要通过“以心观物”“化心为物”“以心观心”三种基本方式进行。如果说散文是在外在世界徘徊,诗就是在内心世界独步,诗是诗人在内心深处的梦呓或独白。
由于诗是一种内视点艺术,其主要任务不是再现客观现实,而是抒发诗人的内心感受,因而,诗歌语言的描绘功能相对缩小,而表情功能大大加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诗与散文虽同属语言艺术,但实质上它们使用的是两种不同的语言:诗歌语言是一种情感性语言,散文语言是一种写实性语言。若用散文的眼光去看诗,就会产生很多误解。比如,不少人就曾认为“白发三千丈”夸张失真,其实,只要明白诗歌语言是一种心灵语言,就不会出现这样的误解了。
诗人必须打碎散文的思维方式,才能真正进入诗歌。另一方面,诗人又不能完全放弃写实语言,使诗歌完全陌生化。
二.诗歌语言的音乐性
就艺术精神而言,诗歌与音乐非常亲近。诗所运用的语言符号颇似音乐语言的音符,它总是力求淡化它的日常意义,以陌生的面貌出现,让我们只能用心去感悟,却不可言说。
从外在形式上看,诗歌有着特有的韵律性,包括语言的节奏性和声调性。简单了解一下中国古代文学史我们就会知道,我国古代的诗都是能入乐歌唱的。从《诗经》到《楚辞》,从乐府民歌到唐诗、宋词、元曲,中国古典诗歌最突出的本质特征就在于抒情性和韵律性。中国诗的音律,是由语音音节的停顿、声韵以及词本身的双声叠字等构成的。以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声声慢》为例,开头的十四个叠字:“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即使不看字义,先听声音,也可以把人们带入一种凄清悲凉的气氛中,感受到诗人孤寂的心境。这就是诗歌语言音乐性的效果。不仅中国古代诗歌有着完美的音韵格律,日本的和歌,西方的十四行诗等,也都是在韵律性方面定型的艺术形式,至今仍被广泛使用。当代的象征主义,甚至把每个词当作音符,把每首诗当作可以演奏的乐曲。即使现代新诗有意打破格律束缚,也同样很讲究音韵美。在现代诗歌史上,“新月派”的代表人物闻一多、徐志摩等就明确提出新诗须具“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命题,并躬身力行。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闻一多的《死水》都是具有音韵美的经典之作。
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之所以说诗的语言是一种音乐语言,除了它具有节奏感和韵律感外,更重要的是其语言符号的价值取向。在读诗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觉察到,诗的语言时常透露出一种散文语言所没有的光辉。一些散文中显得十分平凡的字句,有时忽然会在诗歌中产生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在这里,语言的办事性功能已完全退化,而表情性功能却发展到最大限度,由原来散文语言对意义的追求变为对意味的追寻。当我们听到《蓝色多瑙河》《第九交响乐》《二泉映月》等旋律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有―种或宁静、或悲壮、或深沉的感受;同时,又因听者的文化素养、生活经历、想象力和当时环境的不同而感受各异,并且听者感受到的只是一种意味,很难用“意义”这个概念去界定。诗歌语言也正是这样,当散文语言一旦经过诗人的组构,它就由外在世界的符号变为诗人心灵的音符,就有了―种不可代替性或置换性。
当然,我们不能说诗歌语言就等于音乐语言,诗歌语言虽然追求音乐美,讲究韵律和节奏,但它绝不是单纯的声音艺术,不只是声音的优美回环,它是音与义的交融,即诗在追求意味的同时,也保持着对意义的依恋。倘若没有思想和意义,那它剩下的就只是一堆语言的空壳。另―方面,音乐语言的那些暗示性,有着明显的约定俗成的程式,比如听到哀乐,没有一点音乐细胞的人同样也会感到悲伤的意味,而诗歌的语言则相反,它总是力图排斥一切程式,它永远是独特的个人化的,是上帝都还没有听到的那个声音。
三.诗歌语言的含藏性 随手翻一卷唐诗宋词,我们都会为诗人们心灵的声音所打动,为他们把握语言的恰如其分而拍案叫绝。比如古代的诗人写愁,“愁”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因人因事因境而各不相同,如果要表现它,散文的语言恐怕是力不从心的,而诗歌的语言则让我们如此具体地尝到了“愁”的滋味。有以山喻愁者,赵嘏云:“夕阳楼上山重叠,未抵闲愁一倍多。”有以水喻愁者,李后主云:“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贺铸写愁更高一手,他说:“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以三者比愁之多,尤为新奇,兴中兼比,意味更长。不管是以山写愁,还是以水写愁,以“烟草”“风絮”“梅子黄时雨”写愁,给我们的都是难以述说、愁肠百结的感觉,并且这种感觉因我们的深入体会和想象而愈来愈浓,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对于这种不可言传和言不尽意的抽象事物,诗人们采用了“以实写虚”的手法,于是,便将难以状写之情寄于言外了。下面我们再看一首诗歌:
……
我另怀有目的,不猎艳,不狎邪,只
寻找一个秘密的姓氏被如何放逐到江西
那条古道从哪里出发,多远就
失去了亲人的足迹?
――剑男《前些年在西安》
姓氏有何“秘密”可言?一个姓氏又怎能被“放逐”?这首诗从字面上看,有很多让人看不懂的地方。但我们还是从“江西”这个地理名词找到解读的钥匙:此姓氏即诗人的姓,被放逐的应该是诗人被贬(不宜仅作政治解读)江西的直系祖宗。诗人以实运虚,追宗怀远,到江西去寻自己血脉的根,试图找寻自己从哪里来的答案。这个祖宗是谁?因何事被逐?出发地在何处?与亲人分别时是怎样的情景?这些潜藏在历史深处的“秘密”都在诗人的追问之列。诗人以实喻虚,化虚为实,以空间的 “古道”暗喻一千多年的时间长河,诗人回到现场,将回溯的现在时转换为想象的将来时,“多远就/失去了亲人的足迹?”令人感慨唏嘘,一种悲怆之感油然而生。我们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这几句诗的内容:我们这一支人是怎样从陕西迁到江西的?但诗人没有用这样的散文语言去直叙,而是虚实结合,使文字带有一种庄严的使命感,揪心的疼痛感,深厚的历史感,兼具一种苍凉的人生情味。
这就是真正的诗歌语言,把要表达的东西寄托在语言之外,正如我国古代大批评家刘勰所说的“义生文外”。把情境、心境等显示出来,真正要表达的东西在语言背后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让读者通过具体的形象去体味。简单地说,诗歌语言的含藏性,就是指诗歌的意义隐含在语言的背后,就是我们常说的“言外之意”。一个词、一个句子和一个句群的意义并不限定在他们自身。在一首诗中,它们不再只是传达它们的词典意义,而是赋予更多的暗示性和情感。就像克布鲁克斯所说:“科学的趋势将使共用语稳定,把它们冻结在严格的外延之中;诗人的趋势恰好相反,是破坏性的,他用的词不断地互相修饰,从而破坏彼此间的词典意义。”正是这种“破坏性”,使得诗歌得以形成独特的语言系统,从而把诗的语言从实用性的、字典诠释的一词一义的狭隘理解中解脱出来,通过有限的声音、词汇、语法规则,去表现诗人无限的心灵世界。
这就是诗歌语言的魅力。言外之意、题外之旨留给读者自己去体味,去想象和补充。诗歌语言对散文的破坏,主要是通过象征、暗示、夸张等手段获得的,即古人所说的:“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霭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木写之。”写愁,就是“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当我们“问君能有几多愁”,诗人自然写出“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时,我们仿佛听到诗人胸中的波涛汹涌澎湃,看到诗人穿透语言后的欣慰与洒脱。正如纳德松所说:“世界没有比语言的痛苦更强的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