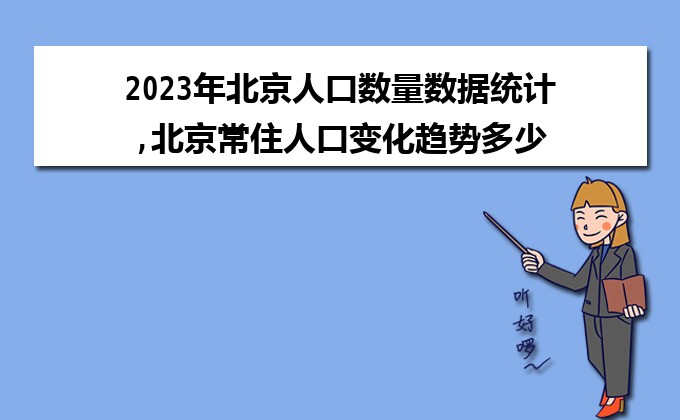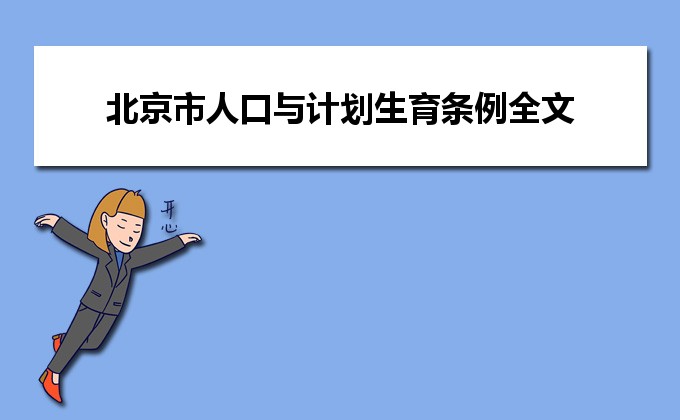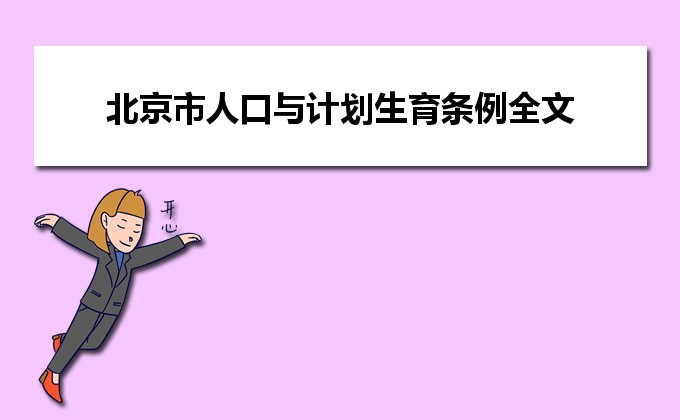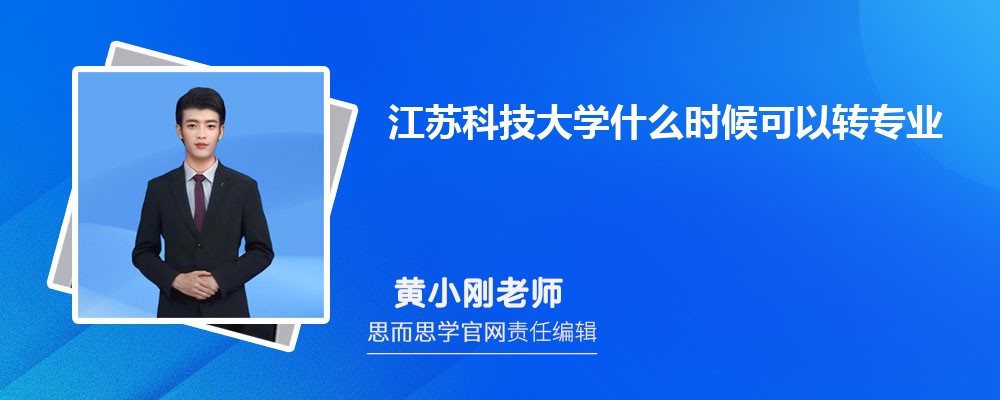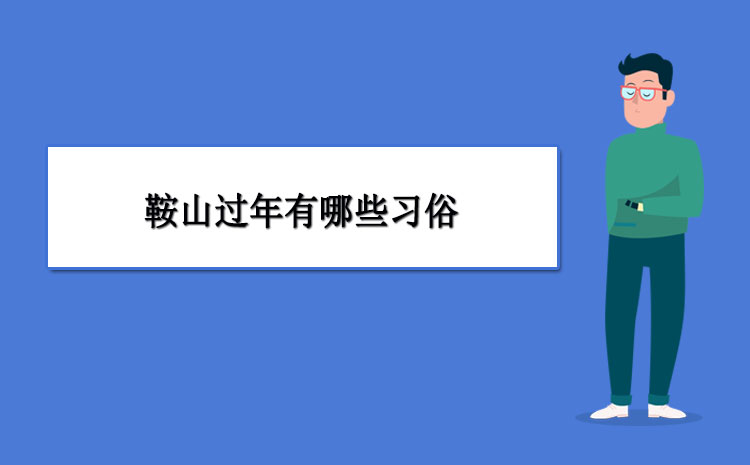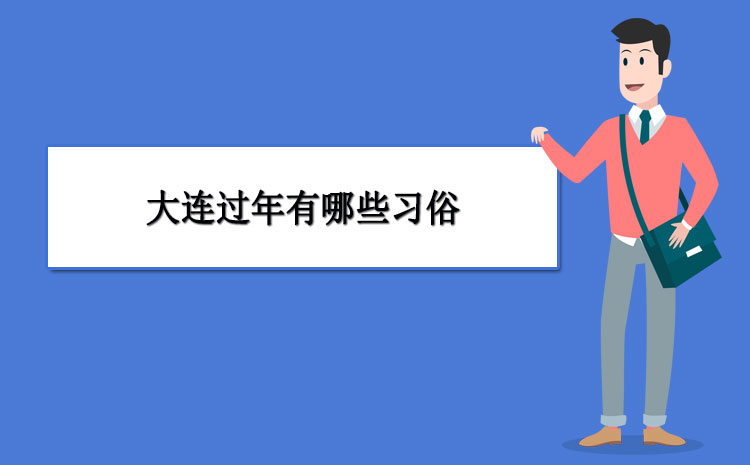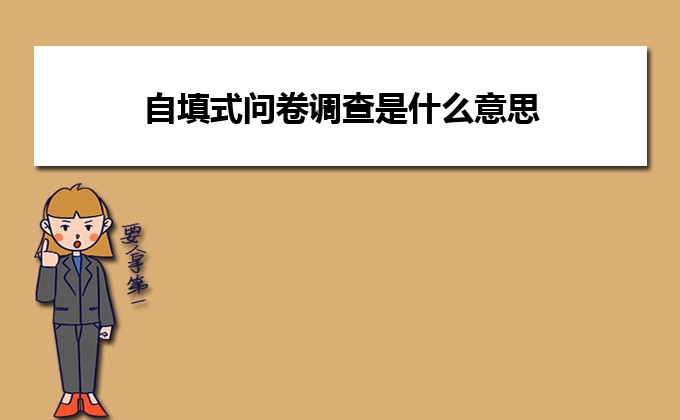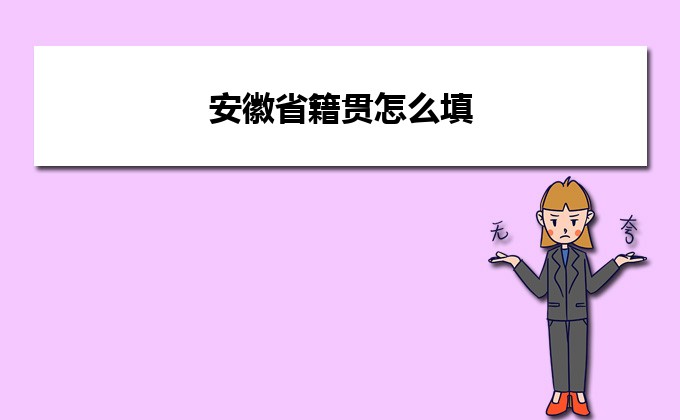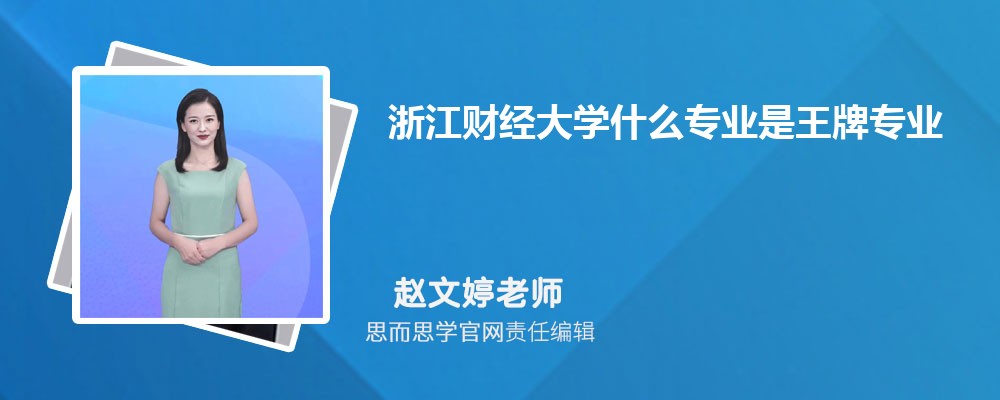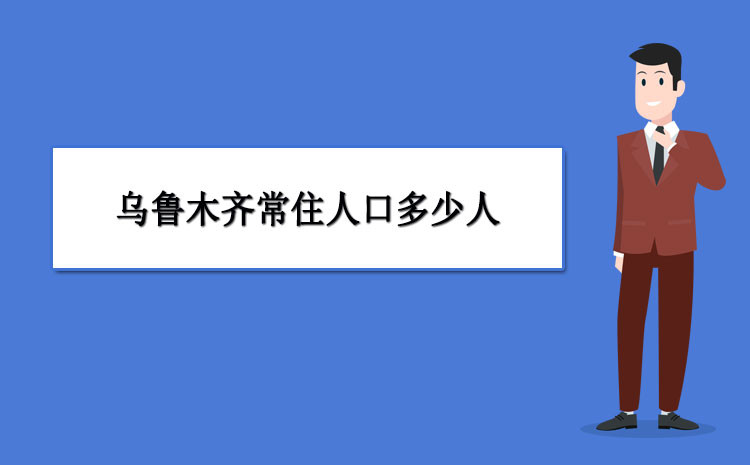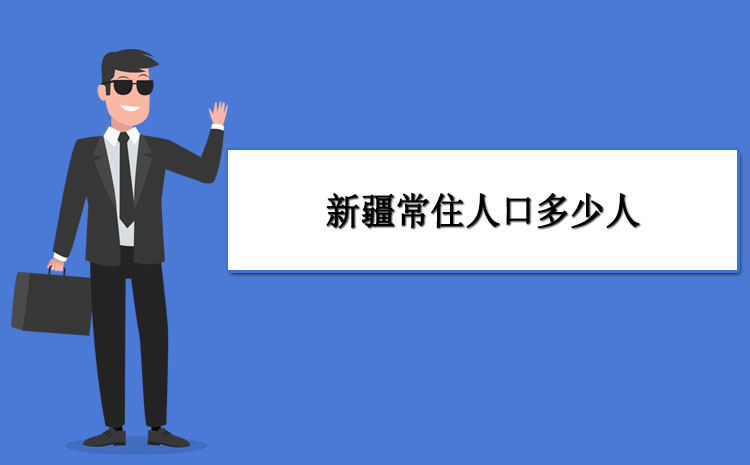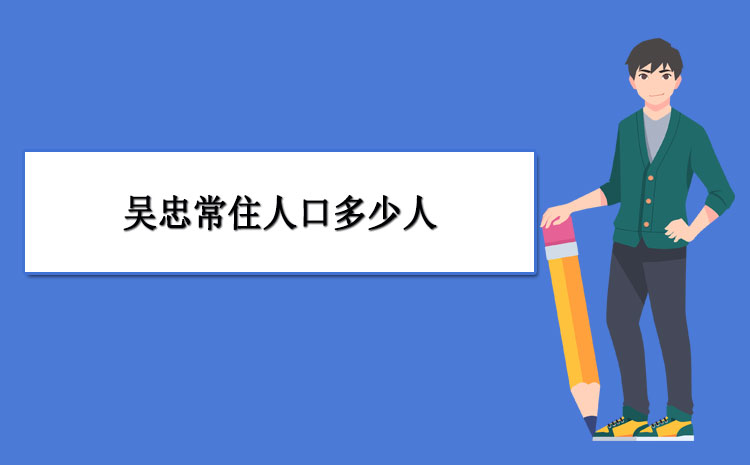2019年末全市常住人口2153.6万人,比上年末减少0.6万人。其中,城镇人口1865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86.6%;常住外来人口745.6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34.6%。常住人口出生率8.12‰,死亡率5.49‰,自然增长率2.63‰。常住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312人,比上年末减少1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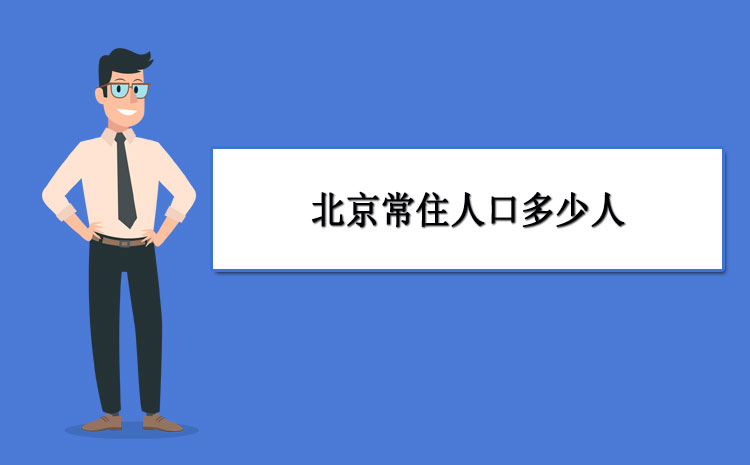
北京人口在减少,环京区域还会吸纳人口么?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待领导层更换后,会不会就被搁置了?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讨论的结论可能不一定很重要,但讨论的逻辑过程非常重要。
1、在“赶人”之下,北京的人口确实在下降,但这不是市场自发的结果,也不是北京作为一座城市竞争力下降导致的结果,而是人为的结果。
市场自由竞争的背景下,一座城市人口量的下降,更多地反映了这座城市竞争力的下降,但北京的人口减少,并不源于北京竞争力的下降,而是来源于高压赶人的结果。也就是说,这是政策的结果,不是市场的结果。
进一步直白点说,北京的人口量下降,缘于政策层面的扬汤止沸,而不是城市基本面层面逐渐恶化下的釜底抽薪。
2、人为导致的北京人口下降,之所以还在“人为”,源于政策还有任性的空间。伴随经济下滑压力的加大,政策上的任性空间越来越小,小至一定阶段,这种“人为”可能就“不人为”或“少人为”了。
中国政策的最大特点之一便是“多变性”。反向思考一下,北京上海如今还可以控制人口,源于当下的经济环境还允许政策层面的继续任性。一旦经济环境恶化到一定阶段,政策任性的空间就会逐渐消失,届时,今日可以控制人口,那日便可吸引人口。
伴随中国经济增速的逐渐“凡人化”,未来中国经济的引擎地必会越来越少,且会逐渐地转移到几个仅有的都市圈。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去年以来,央府三令五申地推动都市圈战略。
在学界,甚至包括一些央府智囊级人物,也在呼吁大城市的人口放开。
8月24日,*主持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参加了本次座谈会。
陆铭认为,“要给大城市发展松绑,要看到大城市在引领现代经济发展当中的引擎的地位。”基于此,他建议,“十四五”期间要加快对城区人口500万以上城市的人口松绑。
陆铭指出,如果看更大范围的城市密度,对比东京等世界大型城市,北京、上海等地的平均人口密度是低的。因为北京和上海目前郊区是可以容纳更多人口的,这也是一个大城市逐渐发展成为连片发展的都市圈的过程。
从发展趋势的角度来说,伴随中国人口问题的下降和GDP增速的下降,包括北京上海等在内的都市圈,可能成为仅剩的中国经济引擎之地,而这必然会倒逼现有政策的修正。
3、即使在人为的高压之下,虽然北京人口总量确实在下降,但北京的远郊人口量却在增加中,所以北京这座城市的远郊化趋势已日益明显,北京政府东迁必然加快这个趋势,而真环京区域是远郊化的覆盖范围。
从全球大城市的发展趋势来看,东京、伦敦、纽约等大城市的发展,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中心化阶段,即人口、资源、资金等全面的内吸,导致城市中心地带的迅速膨胀。
第二个阶段便是远郊化阶段:当一个大城市中心地带的人口越来越集聚,交通越来越堵,房价越来越高时,这个大城市便会开启远郊化趋势,即人口、资源等向远郊集聚。
目前的北京人口流动,正表现出远郊化的趋势,而北京政府的东迁和中央政务区的确立,则加剧了这个过程。
当下远郊化下的北京,人口流动的特点是“中心地带人口量在减少,远郊区的人口在增加”。
2019年,北京内城城六区的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等六区,人口皆在减少,其中朝阳和海淀、丰台成了人口减法的主角,分别减少13.2万人、12.1万人和8万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9年北京各大远郊区皆在加人。
其中,2019年的通州以增加9.7万人和人口增长6.15%,两大指标皆位列榜首,而后,大兴和房山分别增加9.2万人和6.7万人,位列增人榜二三位。相应地,北边的延庆、平谷、怀柔、密云等四个区,人口也在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伴随中央政务区的确立,央府也在政策层面有意推动北京的远郊化:根据此前中央政务区的政策规划,2019年末北京内城的东西城常住人口为193.1万,到2035年减少到170万左右,到2050年进一步下降至155万左右。
所以说,有些人在焦虑于北京人口的减少,却尚未意识到北京人口流动层面的远郊化趋势,而这个趋势,必会利于真环京之地,如东南向的北三县和廊永固等地。
此外,大城市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再中心化。
4、事实胜于雄辩,虽然北京人口在减少,而环京的廊坊,即使在控制落户的2019年,人口量仍然在增加。
现实是最有说服力的答案。
2019年,在自身人口落户冻结和北京人口减少的双压背景下,包括北三县及廊永固霸文大等在内的廊坊常住人口,增加近10万人。
5、从世界人口流动的趋势来说,都市圈必是未来人口的主要流入池。
日本是最好的“先行者”:日本总务省公布的信息显示,2019年日本全国总人口约为1.26亿,连续9年减少。在此背景下,全国各地绝大多数处于人口负增长陷阱中,只有东京都市圈仍然保持人口正增长。
一个国家人口总量正增长疲软,甚至负增长背景下,人口流动会日益的马太效应,经济活力最强的都市圈会成为最强的人口吸入地。
6、南北失衡逐渐替代东西失衡,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失衡表现。在此背景下,不管领导层如何更替,振兴北方,以减缓南北差距会成为一个中长期的央府战略,而振兴北方经济的最好切入地只有京津冀城市群。
政策变动成为一些人担心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未来风险,即某一天领导层更换后,会不会失宠。
以目前的中国经济的失衡状态来看,这个担忧可能是多余的。
当下,中国经济的失衡正从东西失衡转变成南北失衡。在此背景下,可以预见的是,为了平衡中国经济内部的发展不平衡,发展北方,以缩小南北差距,必成为央府不得不做的政策选项。而振兴北方经济的最大切入点和最有效率的切口,必是北京都市圈。这可能也是近期服贸会落户北京和北京自贸区落地背后的重要政策考量吧。
7、真环京的北三县、廊永固等地,伴随通州副中心的崛起和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的推进,在交通、教育医疗、产业等层面的日益北京化,必会加快这些真环京之地的“软性入京”,相应地,这此区域对北漂人口的吸引力也必会水涨船高。
当下的环京,其中长期的城市价值,主要看二点:
首先,看“京”,北京好,环京自然就更好。
其次,看环京与“京”在交通、教育医疗、产业等层面的一体化程度。越北京化,环京的城市价值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