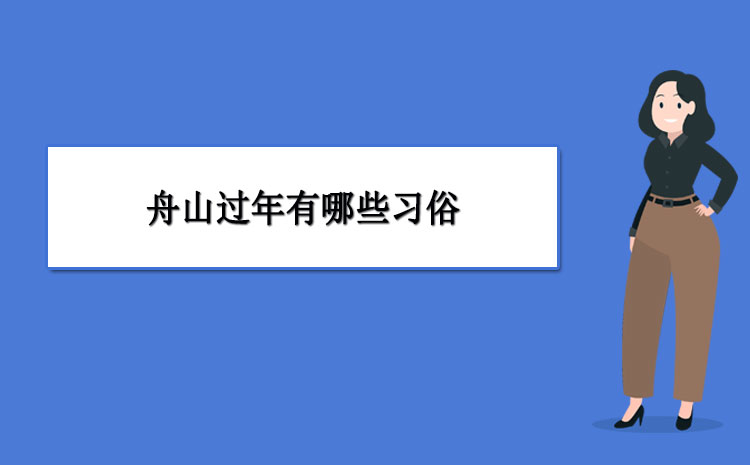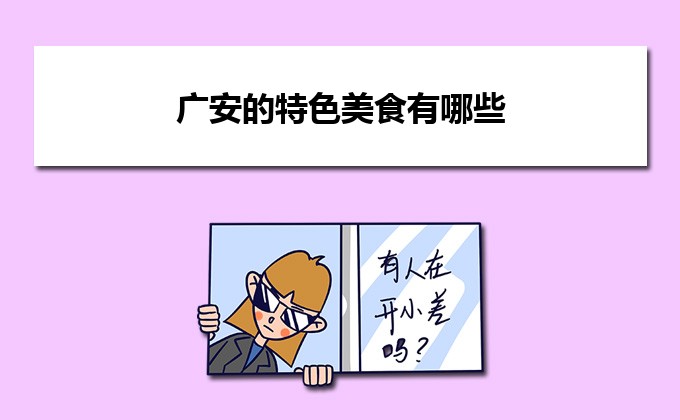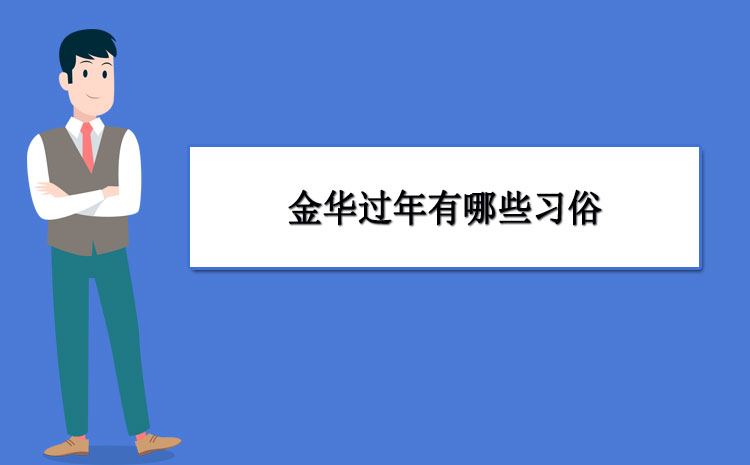台州过年有哪些习俗

温岭位于台州南部,其过年习俗反映出温黄平原一带的大体情形,与台州北部也“异曲同工”。
古时,台州一直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廿三送灶神,廿四掸蓬壅(打扫除尘), 廿五赶长工(给工人发工资回家过年), 廿六克赶市(去市集上购买年货),廿七捣麻糍(做年糕和麻糍),廿八裹粽, 廿九窝冻(烧猪头肉), 三十日早届斫担柴(上午去准备充足的柴禾供正月里用), 三十夜黄昏米筒候五曲(丰盛的晚宴任你吃),正月初一起来拜老爷(去寺庙进香拜佛)。
这首顺口溜简洁押韵,清楚道出了台州人为过年做的种种准备。
廿三“祭灶”,廿四“掸蓬壅”
2019年踩着鼓点不疾不徐而来,目及之处,沿街的红灯笼和“金猪纳福”吉祥物带来的喜庆和祥瑞之气,让人感觉出了浓浓年味。
上世纪70年代的农村似乎普遍贫困。当时母亲虽是乡里(那时还不是镇)农机站的财务,父亲也是村支部书记,平常还是务农为主。家里生活紧巴,虽谈不上缺衣少食,但平常的饭菜,基本都是咸菜配粥。红薯季,便是红薯羹果腹;土豆季,就是蒸煮土豆为粮。
于是,我便盼着过年,因为唯有过年,才有大鱼大肉吃,才有新衣新鞋穿。
腊月廿三,温岭民间开始“拜灶司菩萨”,即祭灶活动,也叫祭拜灶王爷。
如今,老屋灶退出历史舞台,家家户户用上了煤气灶,“祭灶”习俗也随着人们观念的而成为历史。
农历腊月廿四,母亲开始“掸蓬壅”。老房子收拾起来很麻烦,但母亲做事利索,仅仅一天工夫,房子里里外外就焕然一新。一阵洗洗涮涮之后,庭院的角角落落,也便四处晾晒着床单、被子、冬季的衣物。我幼时的年代没有被套,被子是由被单、棉絮和被面缝合而成的。每年临近年三十的某一天,母亲会把堂屋地面来回清扫几遍,而后铺开两张大草席,再叫我帮忙扯开一张被单,垫上棉絮,覆上被面。然后母亲会将四边折成齐齐整整的角,并用顶针辅助穿了粗线的长针缝合里子和被面。过年盖的被子,往往平时不得见,质地上乘,图案精美,尤其是那床龙凤两面织的古香缎被面,最为好看,摸起来也很是光滑柔软。
廿五置年货,最爱打炒米打糕条
农历腊月廿五,父母带我们去置办年货,购买新衣。集市归来,跟我们回家的,往往还有一只昂首挺胸的大公鸡,一只老鸭公,几条鲫鱼,一些腊肠,一大袋炒货,以及每人一套新衣。
其实,年前,小孩子最喜欢的还有爆米花。那时候,专门会有人挑着老式大炮手摇爆米花机,走乡串户,他们一边走一边吆喝“打炒米咯——”于是会有一帮孩子不知从哪里冒出来,追着米花客,一边嚷着“打炒米!打炒米!”(方言,意为“爆米花”,此处“爆”为动词。)也有几位风也似地跑回家,喊爸爸妈妈来打炒米。约莫三五分钟,只见米花客站起身来,把一个长麻袋在地上铺开,然后把米花机口子对准袋口放好。此刻,四周的孩子们纷纷用手堵住自己的耳朵,又害怕又好奇,凑近又退到一定距离,伸长脖子目不转睛地盯着。米花客拉开盖子的栓子,在我眼里仿佛拉开一枚手榴弹,突然“嘣”一声炸响,麻袋瞬间鼓起。之后,白花花脆生生香喷喷甜丝丝的爆米花便被那个来打炒米的人拿个大簸箕欢欢喜喜地装走了。
除此,还有打糕条。就是把大米和糖精倒入一个机器,最后从口子里吐出自来水管粗细的米白色“糕条”,折成30-40厘米长短的一截一截。炒米和糕条拿回家后都会被封入不漏气的塑料袋或缸里,保持脆度,以供正月里当零食吃。
廿八“谢年”,忙起包粽子
农历腊月廿八,是我们家传统“谢年”的日子,即以三牲福礼祈求降福。天蒙蒙亮,父亲就会宰杀一只公鸡,褪毛,并在肚皮下靠近屁股的地方切开一个小口,把内脏洗净,塞回体内,使之看起来完整。但鸡毛不能褪尽,须留下尾巴上三根长羽。接着用红绳把公鸡捆绑出昂首挺胸的形状,再上笼屉蒸熟,同时,另一个大锅里煮着猪头。
母亲会在庭院里设案,放上红漆大托盘,盘里八样东西:猪头、公鸡、鲫鱼、虾、蛤蜊、豆腐、豆芽和年糕。母亲焚香放鞭炮烧纸钱祈拜。
谢年完毕,便忙乎着包粽子。包粽子的活儿,是归父亲管的。每年临近过年,父亲总会去集市上挑选韧性较强的粽叶和棕榈叶,回来烫煮粽叶、清洗,再把棕榈叶撕成一条一条宽度合适的捆扎粽子的带子,以备包粽之用。另外,父亲还会事先把糯米和豇豆分别浸泡好,把红薯去皮并用刨子刨成细丝,再用菜刀剁成细碎的颗粒,又预备好果肉饱满的蜜枣。
包粽子,一般是在农历腊月廿八。看父亲包粽子,年幼的我也便渐渐学会。我会取两张叶子上下错开相叠,在叶尾三分之一处折起形成锥形三角,装入的糯米和叶子边缘齐平,然后,我便将剩下的叶子团起,包严实,最后用棕榈叶条捆扎起来。往往,半天工夫,一个大木桶的粽子便从我们手底下诞生。这足足可以煮两大铁锅的粽子啊!于是,红薯蜜枣粽、豇豆粽和白米粽便轮番在我们餐桌上出现,直至元宵。
年三十,穷人家也上“八碗”
年三十晚上,是最为热闹的。在本地,我们往往称丰盛的一餐为“八碗”。
平时拮据,这一顿,须得八个菜(或者更多)。再穷的人家,也会拿豆芽、笋干、豆腐干、炒面等来凑足数量,但无论怎样,鱼和肉,却是必不可少的。毕竟,肉才能彰显过年的富足,鱼才能表明“年年有余”。而那时候的肉,必是肥肉更受欢迎,因为平时沾少了油腥的人哪,连目光都透着干涩,须等着用肥肉去润滑呢!哪像现在,挑来拣去,非要精瘦的,怕肥肉给自己长了膘。
“八碗”烧好,须得祭祀祖宗,即先让太公太婆爷爷奶奶等先“享用”年夜饭。父亲会在堂屋按一定的方位放置八仙桌,母亲用红漆木托盘端来“八碗”和酒,一一摆开。再取来香案、香烛、纸钱。点起香烛,须倒酒敬三遍,以飨先祖,然后家里按照尊卑一一毕恭毕敬双手合十祭拜,同时口中念着祝愿,求先祖保佑家门顺当财源广进读书人学习优秀等。祭拜完毕之后,开始烧纸钱,以供先祖在冥府之用。
而令我更为欢喜的还有压岁钱。犹记得那时自己拿到五毛钱压岁钱时的心情,那崭新的纸币,仿佛闪着紫色的光芒,被我夹进小人书的书页里,一直压在枕头底下大半年。好似故事里那个要考取功名的书生,枕着它,便会夜夜做黄粱美梦。而现在的孩子,压岁钱的价码一般都得千儿八百。
“除夜”关门炮,初一开门炮
年夜饭后,父亲就出去燃放关门炮,谓之“辞旧”。
接着,父亲便把之前包好的粽子下锅,分两次煮。第一锅,会慢火煮到深夜,第二锅,父亲会在灶坑前看着这微微跳跃的火,一直守到天明。在我年幼的印象里,守夜,已经成了父亲辞旧迎新的一种方式。炉灶里赤黄的火光映着父亲的脸,瞬间有种误当他是神的错觉。
正月初一,父亲早早起来,燃放开门炮,谓之“迎新”。其实,一夜的鞭炮烟花不断,加上兴奋,幼年的我睡睡醒醒。然而瞥见窗外曙色已明,我和妹妹都迫不及待穿上新衣,欢欢喜喜跑出门去。
除夕夜的关门炮,正月初一的开门红,家家户户张贴的红对联和年画,直接让人联想到宋代王安石的那首《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母亲早于我们起床。在曙色微亮的辰光,她便备好新年头一餐需要的东西。正月初一的三餐,几乎是年年固定的模式:早上炒粢饭(温岭本地称其为“炊饭”),是取“炊”的“蒸蒸日上”之意。中午汤年糕,是谓“节节高(糕)升”。晚上煮面条,意取“长寿”。
到元宵为止的整个正月,仿佛就是在不同的亲戚之间走动,吃吃喝喝,拉家常扯鸡毛说蒜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