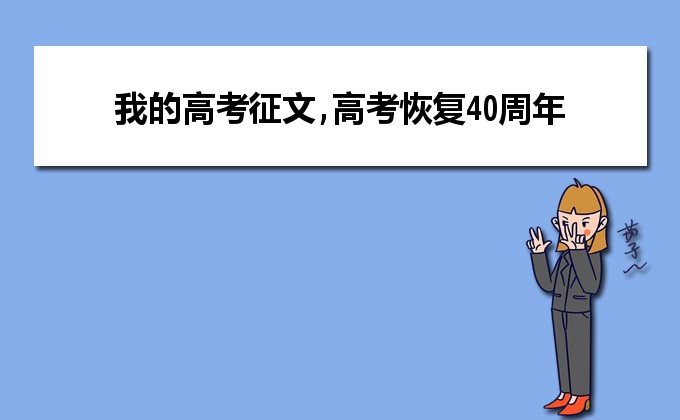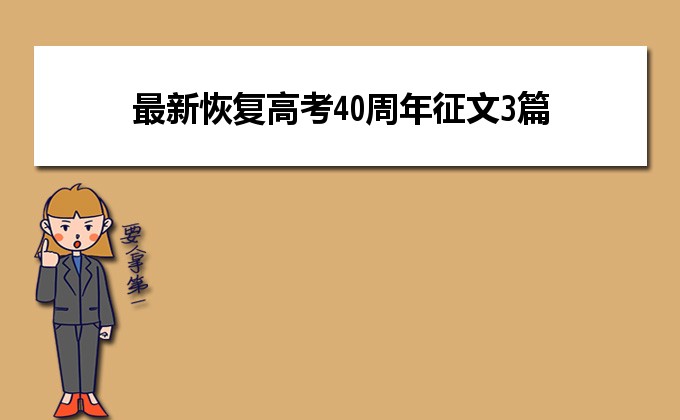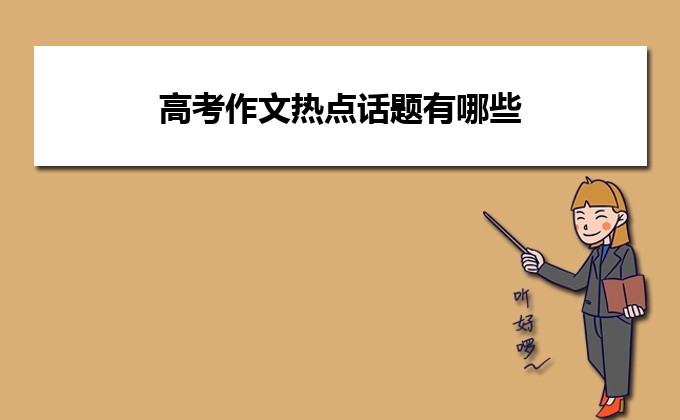我的高考我的大学?恢复高考40年有奖征文【一】
70年代初的淮北农村,使人印象最深的是赶场子。公社电影放映队每月进村一次,这是最热闹的。夕阳下山,夜幕降临,村东头的打麦场上,三根毛竹两竖一横,挂上银幕,柴油发电机嘟嘟响着,放电影?,大伙儿便早早搬着小凳坐了过来,小媳妇,小伙子,孩儿们,这儿一堆,那儿一群,拉着呱,闹着磕,哼着歌……没带凳子就找块砖头、石头坐着,来晚的就站着看,挤不进去的,就踮起脚来看。相恋的男女远远的躲着,看着、看着,人就没了。开映前,生产队长总是扯着嗓子:“大家静一静,今天虽然……但是……”吼上一通,电影开始了。那时的片子大多是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鲜花盛开的村庄》……第二天,放映队移到第二个村庄,爱热闹的人们于是又追了过去,哪怕十里八里,这就是赶场子。
那年,我15岁半,跟随父母从南京下放。我算知青,三个姐姐在南京,大哥下放在洪泽湖边,我排行老五,大家都喊我小五子,老六小学没毕业和我在一起。常常和我一起赶场子的,还有三位年龄差不多的女娃,王平、少萍、晓萍,也是全家下放的。王平伶俐,在家老大,妈妈朱阿姨是个医生,可爱看小说呢,和我妈最能谈得来,她爸爸王叔叔是县武装部的干部;少萍内秀,上面还有个哥哥去当兵了,爸爸是省城体校的十五级老干部;晓萍娇媚在家老二,上面有个姐姐长得和她不像一个妈生的,妈妈是个老师,全家数她最漂亮。每每放电影,“小五子!小五子看电影啦……”,听到喊声,我披着衣服冲出门外。
深秋时节,星空闪烁,我们沿着田间小路,走着山路,拉着手跑着,追逐天上的月亮。月亮也跟着跑了起来,我们轻轻放慢脚步,月亮似乎也停了下来,秋风紧一阵、慢一阵,抚摸着我们,我不禁打了个寒噤,少萍脱下带着余温的外衣给我披上。如水的月光在这无际的田野里弥漫着、飘浮着……我们会情不自禁哼唱:“卖花来呦,卖花来呦,朵朵红花多鲜艳,花儿多香,花儿多鲜,美丽的花儿红艳艳,卖了花儿,来呦来呦,治好生病的好妈妈……”肥沃的土地,贫瘠的生活,唯独赶场子给带着幻想来到山村的我们,平添了多大的欢乐,生活的单调,劳作的苦闷,激发了我们读书的欲望。
日子随着指缝流走,我们真的一起又上了八里之外的打鼓山高中。不久晓萍一家不知何原因搬到固镇县了,北京体院来招生,少萍做了一套广播体操,到北京读书了,爸爸妈妈又回到合肥体校,从此她两人我再也没见过。但那月夜之下,赶场子的情景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不久朱阿姨调到符离集小麦原种场做医生去了,王叔叔又回到县武装部做部长去了。王平也转到了符离集高中读书,我俩一直保持联系,从她那里,我知道了《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的大学》、《在人间》,也知道《红楼梦》、《青春之歌》、《烈火金刚》、《雁飞塞北》……每个星期借书、还书、借书、还书……赶着场子,做着文学的梦。
在那艰苦的日子里,在那山芋干裹腹的岁月中,在那赤着双脚踏在厚厚的泥土里,在那只身一人饿着肚子顶风冒雪往返十五里路求学的追逐中,我的灵魂并不孤独,读书给我带来了希望,文学教会了我抗争!
恢复高考制度77年,我和王平都报了名,填志愿时,我的第一志愿是师范,第二志愿还是师范。如愿以偿,我考上了师范院校。王平考上省城工科院校,拿到入学通知书,小小的山村也热闹起来。那是冬春交际之时,1978年的春天来临了……
屋檐上冰瘤子滴答滴答融化了,院子里的老槐树向空中伸展着,嫩芽在枝条上悄悄躬出,围墙上的紫藤沿着墙裙伸着懒腰,随着春天轻快的脚步,挥挥手,告别父老乡亲,我走向了新的生活。
这是1978年2月28日,我穿着黄军衣、蓝裤子,挎着黄书包,背着三横压两竖的被子,拎着哥哥自己订制的小木箱到学校报到了。此时,哥哥已是炼油厂消防队的一名战士。多少年后,中文系吴老师还记得我报到的情景,的确和别人不一样。
不一样的,77级绝大部分新生是老三届高中或初中毕业生,我是小学68届的。要不是打鼓山高中两年的学习,在千军万马过黄河的高考中,命运之神眷顾了我,我何以会有新的生活?校园的夜晚是宁静的,校园的清晨是沸腾的,博大精深的文学宝库,深深吸引着一个吃了八年山芋干的小伙,我唯有比常人多三倍的努力。
4月24日上午第四节课,是现代汉语,裘老师引导我们分析句子成分:“班长领着我们劳动”,课堂议论纷纷……“班长领着我们,我们劳动;班长领着我们,班长劳动。”从语法的角度,这个句子既是兼语式,也是连动式。想明白了,我大胆地举了手,谈了自己的看法。这时下课铃声响了,我喉咙一痒,一嘴腥味喷出,剧烈地咳了起来,一口口彤红的鲜血落在了地上。我怔住了,同学们惊呆了,同组的上海女同学做过赤脚医生,她说这像支气管扩张,是肺部的血。我被送进医务室。
本来今天该我领饭的。“师范、师范,国家管饭”,同学8个人一组,每天有一人值日,负责领饭。改发饭菜票和伙食津贴是以后的事。我们最期盼的是星期天,家在附近的同学回家了,我们四个人,可以吃上8个人的饭,我已经很满足,不愿再给家里再添任何负担了。
下午体育课我在宿舍休息,同学陪着。四点左右又去了医务室,刚刚坐下,喉咙一痒又开始咯血,量还不少。随即我被送进人民医院,拍片显示左肺中,心边缘有4公分空洞,洞内有积液,初步诊断为肺脓疡。命运之神给我开了个小小的玩笑,我只是受到小小的惊吓,就一个月呗,不用告诉家人。
命运有时真是不可捉摸,正当我准备出院返校时,意外发生了,在病区实习的县医院的一个医生,发现我每晚仍然盗汗,手心还在发热,便给我做了痰检,痰检结果阳性四个+,进一步拍片检查,四公分的洞还在,结论:空洞型肺结核,开放期。噩耗传来,天旋地转,天啦,这怎么可能呢?!无法使人相信,高考入学体检是合格的,新生入学复查我也是合格的!我简直不敢想象,那顶风冒雪往返15里路的求学,那寒夜煤油灯下的苦读,那赤着双脚踏入厚厚泥土艰辛的劳作,那秋夜赶场追月……这一切将可能成为泡影,小鸟刚刚起飞,便折断了翅膀。
谈"核"色变,我似乎等待"死刑"的宣判。同学纷纷涌来,我们有着相似的经历,他们流着泪:“放心!有我们呢!我们忙会帮你的”,系主任陈老师、辅导员李老师等,也来到床前,宽慰,分析:“你要有信心,这个病并不可怕,治愈的例子太多,力争一年后重返课堂。你现在是在籍学生,治病费用不用担心,学校报销,每月生活费学校负责寄给你。”妈妈被召到学校,办完了休学手续,班里派了同学帮助妈妈先把我护送到山村,再联系南京肺结核医院,到南京治疗。
再见了!我的学校,再见了!亲爱的老师,可爱的同学,我要和命运之神交手,我会回来的,我一定会回来的!
我的高考我的大学?恢复高考40年有奖征文【二】
我是二十九岁那年下决心参加高考的。
一九八二年夏天,我任车间主任已经两年。
这天我正在车间里忙着,统计员让我接电话,是康厂长的。
接过康厂长递过来的通知书,我有点懵 ----“兹介绍我厂副厂长杨伏虎同志前往你处参加'现代化管理学习班',请接洽”。
乖乖!我什么时候成副厂长了?康厂长笑着说,这是局里前一段时间决定的。因为你是市里党委厂系统最年轻的厂长,所以让你先去充充电。
我兴冲冲的赶到了省里的这个学习班。但是第一天的第一节课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
看着黑板上密密麻麻的板书,听着老师莫测高深的授课,看着同学们认真的听讲,我有一种使不出劲的感觉 ? 微积分,这是哪位贵宾啊,我听都没听说过!
同班的艾国粹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她见我如此做难,便把她的作业拿来让我抄。我不干,这些基本理论知识不弄懂,怎么学习现代管理理论?
艾工便给我讲解辅导。“三元二次方程知道吗?”我摇摇头。“二元二次方程?”“忘了!““一元一次方程?”“有点儿印象”。
于是就从这里开始讲,整整半个月,作业基本自助完成。但是开始讲现代管理方法时,那些数学模型、矩阵阵列,现代分析又把我弄得焦头烂额。
就从此时,我痛下决心,一定要上大学,我不想被时代淘汰。
但是以我初中二年级的文化程度,距离大学的门槛差距不小,当务之急,是要最大限度的缩小它。
从妹妹建燕那里找了一套三册的数学教材书,便开始啃了起来。
我是厂里抓生产的副厂长,任务压头指标缠身,事务繁杂责任如山。平时连个星期天都很难享受,因此自学数学必须挤出更多的休息时间。
于是我就从每天的两头挖潜。每天早上四点多起床,赶到办公室看书,琢磨各种概念定理公式,再大量的作各种练习题,把各种不懂的地方和难题分别记在不同的纸条上,夹在笔记本里,以备方便请教人师。
上班的时候,每当有了短暂的时间间隙,我便找到那些文化程度比我高的人,取出一张张小纸条,向他们一一请教。弄懂了以后,夜里回家再多作练习以求巩固。
就这样,八三年过去了,八四年过去了,而此时距高考只剩下四个月了,我还要把语文、历史、地理、政治统筹安排。
这时候,由于长年睡眠不足,我的体能已接近极限。有的时候骑着车就想睡过去,说话的时候也会出现思维中断或空白。
我意识到再这样下去恐怕会一事无成,必须跳出眼下的桎梏,全力备战以求胜利。
厂长也是如此走过来的,很理解我,让我把工作交接一下,从二月开始全脱产复习。
在感激振奋的同时,我也感到了压力。这次高考,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为了未来,为了荣誉,为了支持我帮助我的人,拼了!
我推掉了一切杂务和应酬,将家务和生活简化到极处,做一顿饭管一天。
进入四月份,开始冲刺了。我将所有的课本和复习资料摞到沙发旁边,衣不解带的在沙发上生活了一个多月。一睁眼抓着书就看,困了放下书就睡。
为了取得高考的资格,我先参加了成人自学高中考试,顺利取得高中毕业证。又参加了广播电视大学的高考,算是进行了一次实弹演练。到真正的高考结束,已经是荷花初绽的六月了。
虽在意料之中,却也欣慰不已。广播电视大学和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同时给我下发了录取通知书。当我胸佩校徽漫步郑航的校园时,有了一种当年入伍漫步军营的感觉,虚虚的、幻幻的,好像一切都在梦中。